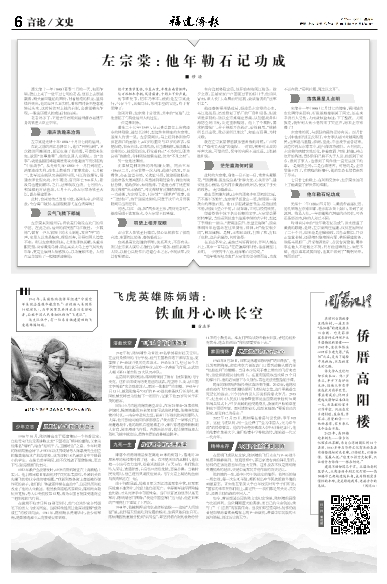左宗棠:他年勒石记功成
文章字数:2565
■穆睦
清光绪十一年(1885)暮春三月的一天,初雨乍晴,鼓山上来了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,他看上去很是羸弱,额头前面隆起的圆骨,衬着削瘦的脸庞,显得格外突出,他的左目几近失明,看东西时会不经意地转过头来,这时候若对上他的右眼,会感觉精光乍现,一股凌厉摄人的威压扑面而来。
老者73岁了,正是去年底刚到福州督办福建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。
潮声浩瀚来沧海
左宗棠是光绪十年(1884)十月廿七到的福州。
在此之前的两江总督任上,他以“目疾加剧”,多次疏请回籍调理,朝廷也准了他的假,可惜假未休完,就因“边事愈棘”,催他急速入京觐见。这“边事”,就是法国侵略越南进而攻击驻越清军而引起的“ 中法战争”。从光绪九年(1883)十一月打到现在,清军连连失利,连本土都受到了军事攻击。七月初三,法军远东舰队突袭福州马尾,马江海战爆发,福建水师仓促应战,全军覆没,官兵阵亡700多人,船政局也遭到破坏,之后,法军转攻台湾。七月初六,朝廷被迫对法宣战,七月十八,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,督办福建军务。
此时,台湾局势已岌岌可危,基隆失守,沪尾受敌,全台海口被封,法国舰艇游弋在台湾海峡!
云气飞腾下郡城
左宗棠来到福州后,将钦差行辕设在北门的皇华馆。在此之前,福州的官民因“马江败挫,一夕数惊”,曾有一户人家院中的木头倒地,发出“呯”的一声,家里人以为是炮响,裸足而奔,引得周围人惶惶不安。所以左宗棠的到来,尤其他手执长鞭,头戴双眼花翎,身穿黄绫马褂,骑在高头大马上意气风发的形象,更是让福州人倍感放心,以为廉颇不老。人们在皇华馆贴了一幅楹联迎接他:
数千里荡节复临,水复山重,半壁东南资保障;
亿万姓轺车争拥,风清霜肃,十闽上下仰声威。
荡节即使节,轺车乃军车,说的是左宗棠此行,气吞斗牛,兵强马壮,东南半壁的安危,终于有保障了。
这副对联,左宗棠十分欣赏,其中的“复临”,让他想起了与两位福州人的过往。
一位是林则徐。
道光二十九年(1849),从云贵总督任上告病还乡的林则徐,途经长沙时,想起住在柳庄的左宗棠,遂派人约请一见。左宗棠闻讯,马上赶到林则徐停泊在湘江的画舫上,65岁的重臣与37岁的布衣,相见恨晚,彻夜长谈,江风吹浪,拍击着船舷,激荡着左宗棠的心,他侃侃而谈,抒发着自己“不为名儒,即为良将”的抱负,令林则徐拍案而起,诧为“不凡之材”。
另一位是沈葆桢。
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。同治五年( 1866)二月,左宗棠第一次入闽,他意气风发,开蚕棉馆,办正谊堂书局,又选址马尾,创建福建船政。当他准备大展鸿图时,突然接到朝廷谕令,调他为陕甘总督。船政伊始,如何能停,于是他力荐丁忧在家的沈葆桢“出主船政”,可沈葆桢有沈葆桢的顾虑,只一力逊谢,左宗棠无奈,只好效“三顾茅庐”故事,也“三造其庐”,终于说服沈葆桢,同意于次年六月母丧服阕后出而任事。
可惜,马江一战,因“两张无主张,两何无奈何”,船政局毁于法军炮火,令左宗棠不胜唏嘘。
叨陪上相开双眼
左宗棠入住钦差行辕后,把心思都放在了援助台湾、布署闽江防务、奏拓船政上。
台湾是南北海道的咽喉,关系甚大,不容有失。所以左宗棠入闽后,以援台为第一要务,他联系南洋大臣,以援台兵轮作出进逼台北之态,牵制法军,使其有所顾虑。
在台湾局势稳定后,他开始布防闽江防务。除夕之夜,正是家家户户团圆过节的好日子,他顶风冒雨,深入长门、金牌前哨巡视,致欲偷袭的“法军引去”。
他还奏拓福州船政局,船政是左宗棠的心血,马江海战后,虽然修复了船厂的厂房和设备,但教训是深刻的,所以左宗棠痛定思痛,从加强战备和海防全局出发,决定重新规划。他上了个奏折,要求拓增炮厂,并于穆源开办铁矿,冶铁自用,“彼挟所长以凌我,我必谋所以制之”,知耻而后勇,为时未晚。
就在左宗棠紧锣密鼓加强备战的时候,广西传来了“镇南关大捷”的捷报。一时间,朝野对主战的呼声大涨,可惜的是,保守的内阁不进反退,主张挟胜和谈。
茫茫瀛海何时晏
此时的左宗棠,身体一日不如一日,常常头晕眼花,气喘腰痛,医生说这是“肝脾火忧,心失所养”,建议他悉心静摄,恰巧同乡黄波前来拜访,便放下手头的政务,一起登临鼓山。
鼓山是闽藩左辅,山中的涌泉寺更是闽刹之冠,若不是军务繁忙,左宗棠早想登山一览,顺便看一看鼓山的摩崖石刻。他11岁起就留意书法,造诣自然不弱,而鼓山壁立千仞,石刻如麻,正可以慢慢欣赏。
望着苍苔半蚀下名公巨卿的文字,左宗棠总要轻轻摩挲,当他看到抗金主战派李纲的名字时,想起了李纲的一首诗,“淹留遂忘归,怅望云海暝”,原来李纲当年也曾站在这里惆怅、徘徊,对“偷安朝夕间”,顿足捶胸。是啊,主和派当政,打败了和,打胜了也和,这茫茫瀛海,何时能晏。
在兼山亭坐定,黄波已写好两首诗,并叫人刻在石上,其中一首写道:“茫茫瀛海何时晏,落落晨星几点明。一夕便传千古迹,他年勒石纪功成。”
“他年勒石纪功成!”左宗棠的泪夺眶而出,功成不必在我,“苟利社稷,死生以之耳”。
落落晨星几点明
光绪十一年(1885)七月廿七的傍晚,福州城的东北隅传来巨响,听说是城墙崩裂了两丈,还在庆幸没有人受伤,大雨就倾盆如注,下了整夜。天刚放亮,就听到大街小巷传来了哭泣声,原来左宗棠薨了!
左宗棠的死,与朝廷的最终妥协有关。四月廿七,《中法新约》正式签订,中方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,法军退出基隆、澎湖,至此,中法战争宣告结束。消息传到左宗棠耳中,他气得浑身颤抖。六月初九,左宗棠的病情突然恶化,伴着痰涌、气喘、抽搐,神志也开始昏迷,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,他想到了家乡,想到了家人,也想到了两件他一直无法放下的事,一是海防全局,二是台湾建省。可惜的是,左宗棠等不到了,在病痛的折磨中,他的生命也悄悄走到了尽头。
七月廿七的晚上,在风雨交加中,左宗棠永远闭上了他渴望了解世界的双眼。
他年勒石纪功成
光绪十二年(1886)四月初二,黄波带着潘纪恩、易孔昭等左宗棠旧部、老乡再次登上鼓山,来到了灵源洞。物是人非,一年前他勒在洞壁的诗仍在,可诗还是那首诗,陪的人却已不同。
吟颂着诗中的“他年勒石纪功成”,泪水浸湿了黄波的眼眶,是呀,左宗棠两任福建,仅仅在福州呆了二十个月,但无论是创建船政、兴办蚕棉馆、开设正谊堂书局,还是组织恪靖援台军、整顿福建防务、增拓马尾船厂、开采穆源铁矿、奏议台湾建省,哪件事在他人不是避之不及,只有他迎难而上,肩任不辞。他以诸葛武侯自居,也真正做到了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。
清光绪十一年(1885)暮春三月的一天,初雨乍晴,鼓山上来了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,他看上去很是羸弱,额头前面隆起的圆骨,衬着削瘦的脸庞,显得格外突出,他的左目几近失明,看东西时会不经意地转过头来,这时候若对上他的右眼,会感觉精光乍现,一股凌厉摄人的威压扑面而来。
老者73岁了,正是去年底刚到福州督办福建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。
潮声浩瀚来沧海
左宗棠是光绪十年(1884)十月廿七到的福州。
在此之前的两江总督任上,他以“目疾加剧”,多次疏请回籍调理,朝廷也准了他的假,可惜假未休完,就因“边事愈棘”,催他急速入京觐见。这“边事”,就是法国侵略越南进而攻击驻越清军而引起的“ 中法战争”。从光绪九年(1883)十一月打到现在,清军连连失利,连本土都受到了军事攻击。七月初三,法军远东舰队突袭福州马尾,马江海战爆发,福建水师仓促应战,全军覆没,官兵阵亡700多人,船政局也遭到破坏,之后,法军转攻台湾。七月初六,朝廷被迫对法宣战,七月十八,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,督办福建军务。
此时,台湾局势已岌岌可危,基隆失守,沪尾受敌,全台海口被封,法国舰艇游弋在台湾海峡!
云气飞腾下郡城
左宗棠来到福州后,将钦差行辕设在北门的皇华馆。在此之前,福州的官民因“马江败挫,一夕数惊”,曾有一户人家院中的木头倒地,发出“呯”的一声,家里人以为是炮响,裸足而奔,引得周围人惶惶不安。所以左宗棠的到来,尤其他手执长鞭,头戴双眼花翎,身穿黄绫马褂,骑在高头大马上意气风发的形象,更是让福州人倍感放心,以为廉颇不老。人们在皇华馆贴了一幅楹联迎接他:
数千里荡节复临,水复山重,半壁东南资保障;
亿万姓轺车争拥,风清霜肃,十闽上下仰声威。
荡节即使节,轺车乃军车,说的是左宗棠此行,气吞斗牛,兵强马壮,东南半壁的安危,终于有保障了。
这副对联,左宗棠十分欣赏,其中的“复临”,让他想起了与两位福州人的过往。
一位是林则徐。
道光二十九年(1849),从云贵总督任上告病还乡的林则徐,途经长沙时,想起住在柳庄的左宗棠,遂派人约请一见。左宗棠闻讯,马上赶到林则徐停泊在湘江的画舫上,65岁的重臣与37岁的布衣,相见恨晚,彻夜长谈,江风吹浪,拍击着船舷,激荡着左宗棠的心,他侃侃而谈,抒发着自己“不为名儒,即为良将”的抱负,令林则徐拍案而起,诧为“不凡之材”。
另一位是沈葆桢。
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。同治五年( 1866)二月,左宗棠第一次入闽,他意气风发,开蚕棉馆,办正谊堂书局,又选址马尾,创建福建船政。当他准备大展鸿图时,突然接到朝廷谕令,调他为陕甘总督。船政伊始,如何能停,于是他力荐丁忧在家的沈葆桢“出主船政”,可沈葆桢有沈葆桢的顾虑,只一力逊谢,左宗棠无奈,只好效“三顾茅庐”故事,也“三造其庐”,终于说服沈葆桢,同意于次年六月母丧服阕后出而任事。
可惜,马江一战,因“两张无主张,两何无奈何”,船政局毁于法军炮火,令左宗棠不胜唏嘘。
叨陪上相开双眼
左宗棠入住钦差行辕后,把心思都放在了援助台湾、布署闽江防务、奏拓船政上。
台湾是南北海道的咽喉,关系甚大,不容有失。所以左宗棠入闽后,以援台为第一要务,他联系南洋大臣,以援台兵轮作出进逼台北之态,牵制法军,使其有所顾虑。
在台湾局势稳定后,他开始布防闽江防务。除夕之夜,正是家家户户团圆过节的好日子,他顶风冒雨,深入长门、金牌前哨巡视,致欲偷袭的“法军引去”。
他还奏拓福州船政局,船政是左宗棠的心血,马江海战后,虽然修复了船厂的厂房和设备,但教训是深刻的,所以左宗棠痛定思痛,从加强战备和海防全局出发,决定重新规划。他上了个奏折,要求拓增炮厂,并于穆源开办铁矿,冶铁自用,“彼挟所长以凌我,我必谋所以制之”,知耻而后勇,为时未晚。
就在左宗棠紧锣密鼓加强备战的时候,广西传来了“镇南关大捷”的捷报。一时间,朝野对主战的呼声大涨,可惜的是,保守的内阁不进反退,主张挟胜和谈。
茫茫瀛海何时晏
此时的左宗棠,身体一日不如一日,常常头晕眼花,气喘腰痛,医生说这是“肝脾火忧,心失所养”,建议他悉心静摄,恰巧同乡黄波前来拜访,便放下手头的政务,一起登临鼓山。
鼓山是闽藩左辅,山中的涌泉寺更是闽刹之冠,若不是军务繁忙,左宗棠早想登山一览,顺便看一看鼓山的摩崖石刻。他11岁起就留意书法,造诣自然不弱,而鼓山壁立千仞,石刻如麻,正可以慢慢欣赏。
望着苍苔半蚀下名公巨卿的文字,左宗棠总要轻轻摩挲,当他看到抗金主战派李纲的名字时,想起了李纲的一首诗,“淹留遂忘归,怅望云海暝”,原来李纲当年也曾站在这里惆怅、徘徊,对“偷安朝夕间”,顿足捶胸。是啊,主和派当政,打败了和,打胜了也和,这茫茫瀛海,何时能晏。
在兼山亭坐定,黄波已写好两首诗,并叫人刻在石上,其中一首写道:“茫茫瀛海何时晏,落落晨星几点明。一夕便传千古迹,他年勒石纪功成。”
“他年勒石纪功成!”左宗棠的泪夺眶而出,功成不必在我,“苟利社稷,死生以之耳”。
落落晨星几点明
光绪十一年(1885)七月廿七的傍晚,福州城的东北隅传来巨响,听说是城墙崩裂了两丈,还在庆幸没有人受伤,大雨就倾盆如注,下了整夜。天刚放亮,就听到大街小巷传来了哭泣声,原来左宗棠薨了!
左宗棠的死,与朝廷的最终妥协有关。四月廿七,《中法新约》正式签订,中方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,法军退出基隆、澎湖,至此,中法战争宣告结束。消息传到左宗棠耳中,他气得浑身颤抖。六月初九,左宗棠的病情突然恶化,伴着痰涌、气喘、抽搐,神志也开始昏迷,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,他想到了家乡,想到了家人,也想到了两件他一直无法放下的事,一是海防全局,二是台湾建省。可惜的是,左宗棠等不到了,在病痛的折磨中,他的生命也悄悄走到了尽头。
七月廿七的晚上,在风雨交加中,左宗棠永远闭上了他渴望了解世界的双眼。
他年勒石纪功成
光绪十二年(1886)四月初二,黄波带着潘纪恩、易孔昭等左宗棠旧部、老乡再次登上鼓山,来到了灵源洞。物是人非,一年前他勒在洞壁的诗仍在,可诗还是那首诗,陪的人却已不同。
吟颂着诗中的“他年勒石纪功成”,泪水浸湿了黄波的眼眶,是呀,左宗棠两任福建,仅仅在福州呆了二十个月,但无论是创建船政、兴办蚕棉馆、开设正谊堂书局,还是组织恪靖援台军、整顿福建防务、增拓马尾船厂、开采穆源铁矿、奏议台湾建省,哪件事在他人不是避之不及,只有他迎难而上,肩任不辞。他以诸葛武侯自居,也真正做到了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。